十五年磨一剑:资本短视下,安科生物杨林博士的全球首款CAR-T突围战

“从实验室到临床,我们用了15年。如果资金能跟上,这款药或许能早几年救更多人。”当博生吉医药创始人杨林博士看到PA3-17注射液获准进入关键性II期临床试验的通知时,这位在中国最早提出肿瘤细胞疗法概念的科学家,语气里满是感慨。2024年,安科生物参股的博生吉及博生吉安科收到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的会议纪要,标志着这款全球首款靶向CD7的自体CAR-T细胞治疗产品向上市迈出关键一步,但这一步,比预期晚了太久。
2010年,杨林博士创办博生吉,彼时细胞免疫治疗在国内尚属空白领域。他带领团队率先攻坚CD7阳性血液淋巴系统恶性肿瘤这一难题——这类疾病复发难治,传统疗法疗效有限,而CD7靶点的研发更是因“CAR-T细胞相互残杀”“肿瘤细胞残留”等技术难关,让全球众多团队望而却步。博生吉自2012年起深耕CD7单域抗体研发,历经免疫毒素、CAR-NK等技术路径探索,最终突破性地采用非基因编辑策略,解决了安全性与疗效的平衡问题,前期临床试验中更是取得了100%客观缓解率、近90%完全缓解率的优异数据。

然而,技术突破并未换来资本的持续青睐。医药研发“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性,与资本对即时回报的追求形成尖锐矛盾。博生吉的融资历程清晰地折射出这种困境:2012年获得天使轮投资后,直到2015年才迎来安科生物的战略投资,2021年完成A轮融资时,距离公司成立已过去11年,而此时PA3-17注射液已进入临床申报阶段。反观CAR-T领域整体融资环境,2021年后行业遇冷,2024年平均融资规模跌至3100万美元,仅为巅峰时期的一半,投资者对缺乏短期回报的早期研发项目愈发谨慎。
资金短缺直接拖累了研发进程。这款2021年就获得中美两国临床批准、2025年被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的全球首创药物,在杨林博士15年的坚守下,至今仍在临床试验阶段。要知道,CAR-T药物的研发每推进一个阶段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撑,从细胞制备工艺优化到多中心临床数据积累,任何环节的资金断流都可能导致项目停滞。博生吉虽开发出低成本全自动制备工艺,却因资金限制无法快速扩大临床规模。
市场对创新药企的差异化态度更显讽刺。当同为创新药企的百利天恒能获得市场激烈反应与全力支持时,参股博生吉的安科生物却未能撬动同等规模的资本关注。在2024年CGT领域融资寒冬中,虽有ArsenalBio等企业获得数亿美元融资,但这类资金多流向进展明确或有巨头背书的项目,像博生吉这样深耕冷门靶点、依赖长期技术积累的企业仍难获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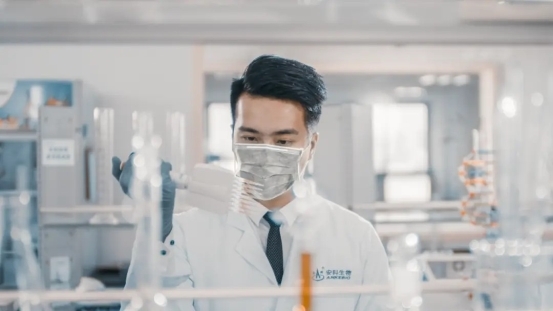
“这款药能让普通患者用得起,这是我们的初心。”杨林博士团队研发的PA3-17注射液,凭借工艺优化大幅降低成本,本可成为血液肿瘤患者的福音。但资本的短视,让这款全球首创药物的上市之路充满波折。如今,随着关键性II期临床的启动,博生吉终于看到曙光,但多年的延误足以让无数患者错失生机。
在医药创新的赛道上,杨林博士的“灰头土脸”是中国科研者坚守的缩影。当PA3-17注射液最终走向市场时,我们或许更该思考:若资本能多一份耐心,少一份对即时利益的追逐,多少像杨林这样的科研者能少些煎熬,多少救命药能提前抵达患者身边。这不仅是对科研精神的尊重,更是对生命价值的守护。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15
环保板材成家居刚需,千年舟以ENF级技术领跑行业
精神分裂症治疗破局者,康玉春主任40年深耕中西结合,用针药为患者点亮重生之光
赛立复研究院:赛立复力活元最佳服用指南,必须收藏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当再植无望,手指再造为患者重塑“完整人生”
一文了解光模块10大厂商!了解了他们,你就了解了光模块发展史
【因耳美丽】小耳畸形,重塑一个漂亮耳朵,当前的主流方案有哪些
相关新闻
家电推荐
家电图片
新闻排行
- 1
中国影片《绝望》入围 2025 柏林国际环球电影节主创受邀出席颁奖盛典
- 2
伊萨推出升级版SUPRAREX™ PRO自动化切割设备:更大尺寸、更强结构、更高安全性、更易维护
- 3
优酷综艺《快乐趣吹风》第三期开播 “高能抽风团”闯关团播新赛道
- 4
地上铁构建“技术-车型-服务”协同体系,全力破局城际物流电动化
- 5
京东3C数码电玩惊喜日引爆消费热潮 超1000个品牌成交额翻倍
- 6
预告!星火社吕诚将推 “星星之火” 线上课堂,哲思 + 投资赋能公益新生态
- 7
卡莱米路以全产业链与权威认证树立品质标杆
- 8
孙兵文律师登 CCTV-7,专业形象获国家级平台背书
- 9
北京光业律师事务所荣膺央视CCTV-12品牌展播
- 10
Hape重装亮相2025中国玩具展:多维实力助推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