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教授谈新公司法下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边界重构及中美治理模式比较
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权力的制衡。在 (2016)黔民终 546号案件里,贵州高院明确支持股东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撤销董事会决议,这种“股东会中心主义”曾是中国公司治理的典型代表。然而,2023年新《公司法》的颁布,正促使治理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董事会开始拥有独立的决策空间,股东会直接推翻董事会决议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变革背后,是向国际主流治理模式的靠近,也是对中国市场需求的回应。对此,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教授,原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刘忠进行了分析:

一、治理模式的转变:从股东会中心到董事会中心
传统中国模式(股东会中心主义):
权力聚焦:股东会被认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在理论上对公司所有重大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
董事会角色:董事会更多地被当作股东会的执行部门或代理人,其决策权依赖于股东会的明确或默认授权,缺乏独立的法定地位。
实际问题:这使得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过度干涉日常运营,董事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难以施展,公司决策效率不高,而且权责不明确。
美国主流模式(董事会中心主义):
法定权力赋予:以《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为代表的美国州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的业务和事务由董事会管理或在董事会指导下管理,这是法律给予董事会的核心权力。
股东会权力法定限制:股东会的权力被明确限制在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如选举董事、批准根本性变更如合并、章程修订等)。在此范围之外,股东会无权直接干涉董事会的经营决策。
商业判断规则保护:法院在审查董事会决策时,通常运用商业判断规则,假定董事基于充分信息、善意且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存在欺诈、违法或严重过失,否则法院不会干预董事会的商业决策。
新《公司法》的转型定位:
新法虽未像美国法那样明确宣称“公司由董事会管理”,但其修订条款明显强化了董事会的法定职权与独立性:
职权独立:董事会职权不再完全依赖股东会授权,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如第 67条等)拥有明确的、相对独立的决策范围(如决定经营计划、投资方案、内部机构设置、高管任免等)。
股东会无权直接推翻:这是新旧法最关键的变化。在新法体系下,股东会不能以“最高权力机关”的身份直接否决或撤销一个在董事会法定职权范围内、程序合法的决议。这是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迈进的重要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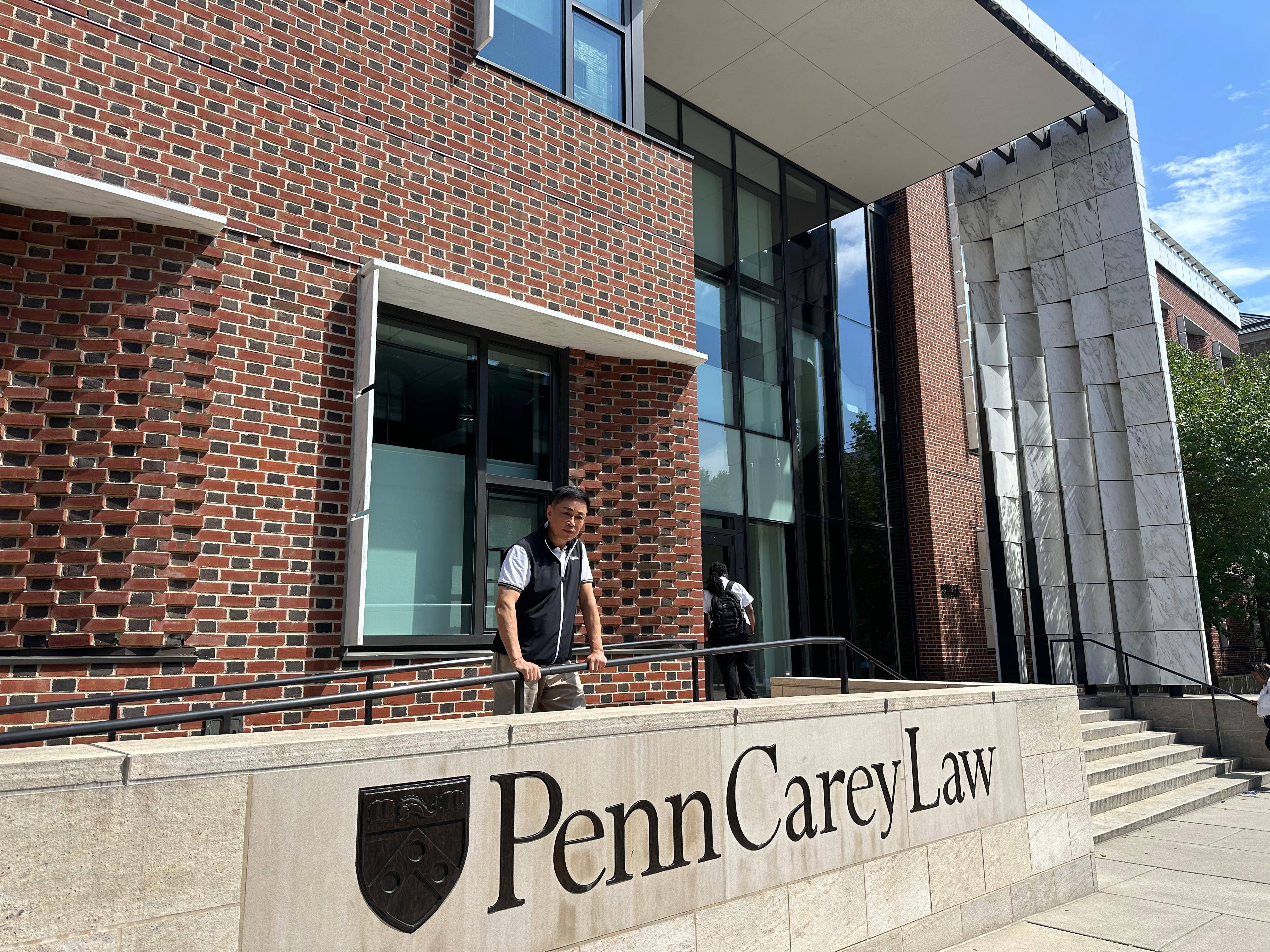
刘忠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二、新《公司法》的重要进步:构建清晰的权力与救济框架
1.明确职权边界,确立董事会独立性:新法第 59条、第 67条等条款较为清晰地列举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主要职权。例如,修改章程、增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等重大变更专属于股东会(需 2/3以上表决权通过,第 66条),而经营决策、内部管理等权力明确赋予董事会。进步意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股东会“无所不能”的传统观念,为董事会的专业经营提供了法定空间,符合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趋势,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和专业性。
2.决议瑕疵分类处理,救济途径细化:新法第 25、26、27条系统构建了股东(会)挑战董事会决议的路径,严格限制股东会直接干预:决议无效(第 25条):针对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如董事会越权决定修改章程、增减资等专属股东会权限事项)。决议可撤销(第 26条):针对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股东需在决议作出后 60日内(未被通知的股东自知道 /应当知道起算)或决议作出后 1年内起诉。决议不成立(第 27条):针对根本未形成有效决议的情形(如未开会、未表决、出席 /表决权数不足、表决结果未达标)。进步意义:该框架借鉴了比较法经验(包括美国法对董事会决议效力的司法审查模式),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救济标准,将纠纷引导至司法解决,避免了股东(尤其大股东)在公司内部的任意干预,增强了公司治理的法治化和可预期性。60日 / 1年的除斥期间设计也促使股东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稳定。
3.确立股东会间接制衡机制:新法第 59条明确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董事。这是股东会对董事会最核心、最有效的制衡手段。进步意义:承认股东作为所有者的最终控制权,但要求其通过法定程序(选举董事)间接影响未来

刘忠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三、剖析新法相较美国实践的差距与挑战
1.职权划分的模糊之处与剩余权力归属的不明确关键问题:新法在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列举方面存在交集或模糊之处,例如“经营方针”与“经营计划 /投资方案”的界限、“重大”事项的认定标准不够清晰。并且,法律未对未被列举的“剩余权力”应归属于股东会还是董事会作出明确界定。美国的情况:特拉华州等的公司法明确将公司管理权赋予董事会,股东会仅拥有法定和章程明确规定的权力,剩余权力自然归董事会所有。这种明确的权力归属机制大幅减少了争议。影响: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种模糊区域极易引发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争斗,成为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的理由,从而削弱新法所确立的董事会独立性。因此,急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来明确“剩余权力归董事会”这一原则。
2.股东救济的成本与效率难题成本过高:股东挑战董事会决议的唯一有效方式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第 25 - 27条)。然而,诉讼程序繁杂、耗时久、费用高,这对小股东极为不利。美国的模式:美国股东挑战董事会决策的主要途径是派生诉讼,虽然其有一定门槛(如需先向董事会提出请求、证明“请求无用”等),但美国发达的集团诉讼制度、风险代理机制以及法院对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慎运用,在保护股东权益和尊重董事会决策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此外,美国上市公司股东可通过投票权积极影响董事选举。影响:高昂的诉讼成本可能使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对违法违规的董事会决议望而却步,导致救济途径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无法有效约束董事会的权力滥用。所以,需要探索更为便捷、低成本的救济途径,例如完善公司内部异议机制、借鉴商业判断规则以缩小司法审查范围、降低派生诉讼门槛等。
3.配套制度供应短缺董事信义义务规则不够精细:新法第 180条对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只是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像美国判例法那样详尽、可操作的规则,如用于审查利益冲突交易的“完全公平测试”、“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标准等。独立董事制度效能有待提高:新法虽强化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职权(第 121条),但总体而言,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保障、履职激励和约束机制仍需强化,其监督制衡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累积投票制普及程度低:该制度(第 108条)有助于小股东推选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进入董事会,是股东间接制衡董事会的重要机制,但在实践中采用率较低,章程默认规则为普通投票制。美国的配套:美国发达的董事责任保险、成熟的独立董事市场、相对完善的董事会委员会制度(审计、薪酬、提名)以及特拉华法院对信义义务的精妙阐释,共同构成了支撑董事会中心主义有效运行的关键配套。影响:缺乏强有力的配套制度,仅依靠形式上的职权划分,难以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问责,可能造成权力滥用或责任虚化。
4.商业判断规则的缺失核心问题:新法未明确规定商业判断规则,法院在审查董事会经营决策的合理性时,缺乏清晰的司法克制原则。美国的基础:商业判断规则是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司法基石。它假定董事决策是基于充分信息、善意且符合公司最佳利益,除非原告能证明存在欺诈、违法、利益冲突或重大过失,否则法院不会干预。这极大地保护了董事的经营裁量权。影响:缺乏这一规则,可能导致法院过度介入董事会的商业决策,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评判决策优劣,使得董事在决策时顾虑重重,抑制其创新和冒险精神,最终损害公司利益和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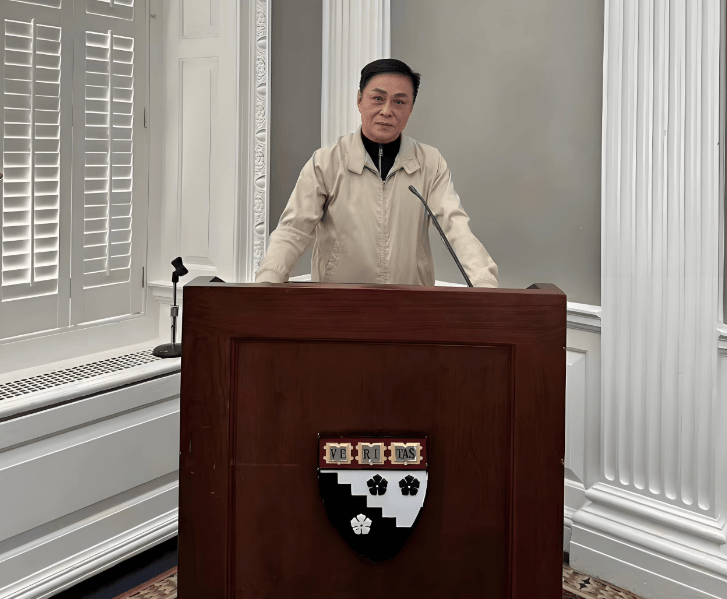
刘忠教授在哈佛给学生授课四、结语:构建董事会专业经营与股东有效监督的平衡新《公司法》在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划分上的转变,是中国公司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打破了股东会“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为董事会独立行使经营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构建的决议瑕疵类型化救济体系也显著提升了治理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这些进步表明中国公司治理正在努力与国际先进实践(特别是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核心原则)接轨。然而,清晰的职权列举仅仅是开端。与美国成熟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实践相比,新法在剩余权力归属、股东救济成本、配套制度(尤其是精细化的信义义务规则和缺失的商业判断规则)以及独立董事效能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未来的完善方向需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公司经营管理权归属于董事会”这一基本原则以及剩余权力的归属。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明确权力的归属是构建科学治理体系的基石,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能够提供权威性的界定,确保公司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其二,于司法审查环节引入并发展契合中国国情的商业判断规则。在中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尊重董事会的商业决策空间意义重大。这一规则的引入与发展,有助于在司法层面保障董事会在合理商业决策范围内的自主性,避免过度的司法干预影响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
其三,切实削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维权成本,探寻诉讼外的有效救济机制。小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高昂的维权成本会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探索诉讼外的救济机制,能够为小股东提供更多元化的维权途径,增强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有效性。
其四,持续优化董事信义义务规则,强化独立董事制度的实际效果,推广累积投票制等配套措施。董事信义义务规则的完善能够促使董事更好地履行对公司和股东的义务,独立董事制度实效的强化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累积投票制的推广则有利于保障股东的表决权,这些配套措施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唯有如此,才能够在中国的环境下真正构建起董事会专业独立经营、股东有效监督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生态,进而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
本文基于新《公司法》条文及立法精神,从中美比较的视角展开分析。在具体的案例当中,针对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限争议,必须依据章程的具体约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及其程序的合规性、相关的证据链条等多维度进行综合判断。在企业治理实践中,建议强化章程修订与程序合规审查,这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权限争议,保障公司治理的有序性与合法性。 (文/刘忠)
责任编辑:kj015
贵阳看牙想舒适?德韩口腔是优选!系统化诊疗 + 无痛体验,重新定义舒适化口腔服务
凸嘴Girl必看变美公式!讲清脸型的底层逻辑!辽宁杏林
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第三季8月30日开幕,助力响应香港“八大中心”定位
权威测评!2025年8月全国高校国际本科项目实力TOP5盘点
八月最新!2025年中外合作办学top9权威测评
八月最新!2025 全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力盘点
相关新闻
家电推荐
家电图片
新闻排行
- 1
【青春助力“百千万”】广师大雏菊突击队赴黎埠展青年力量,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 2
刘忠教授谈新公司法下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边界重构及中美治理模式比较
- 3
青春志愿行,文明进社区!南昌理工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志愿服务队在丰城玉龙社区绽放光彩
- 4
跟龚俊学早秋穿搭解锁少年感 上京东入手舒适睡衣、时髦鞋服等官方立减12%
- 5
艺术之花绽放在社区,青春力量温暖人心|南昌理工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暑期“三下乡”走进南昌市青云谱区青峰...
- 6
快门工坊自拍亭:从场景到运营 这篇干货帮你避开所有坑
- 7
人工智能政策发布,九科信息积极响应并领跑国央企AI Agent商业化落地
- 8
【喜报】!金天弘全自主万分之一级MEMS硅谐振压力芯片重磅核心技术荣登北京市科协25年科技荣耀榜单!
- 9
2025年中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总决赛胜利收官!
- 10
361度2025中期业绩飘红,电商业务增长势头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