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恩典,自主是回应 ——读倪考梦《自主论》有感
文 / 叶文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科奠基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创始人)
前些日子,收到学生倪考梦寄来的新书《自主论》。封面干净沉静,题目却颇具分量。他说这本书是他追问自己、也追问这个时代的一种尝试。我拿起书,翻读数日,竟时时有共鸣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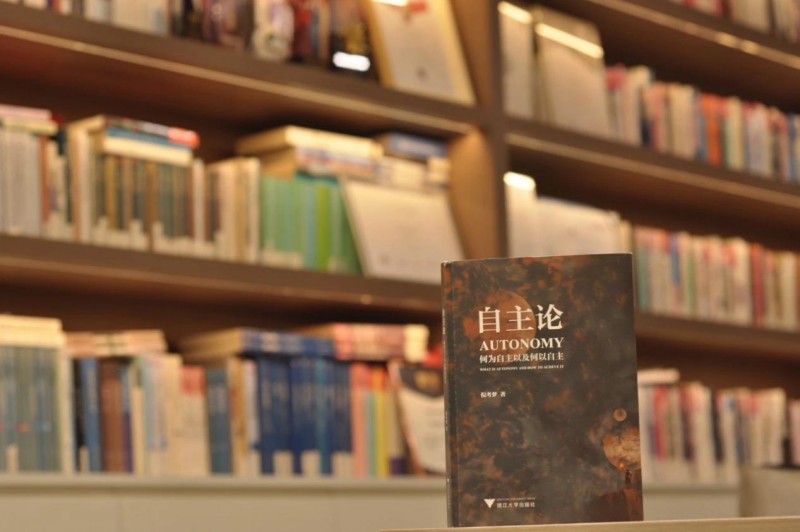
考梦这本《自主论》,给我一种既熟悉又欣喜的感觉。熟悉,是因为他书中提出的“自主三角形”理论,与我多年来关于资源环境与社会选择之间关系的观察不谋而合。欣喜,则是看到有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把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成为自己”,放到一个如此复杂而真实的社会结构中加以探讨,给予它制度、文化与生态维度上的延展。
我与考梦相识已有十五年。他曾是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后来也曾参与温州的生态文明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实践。他是个有热情、有行动力的青年,如今能写出这本将心理学、社会结构、技术伦理等领域交织在一起的思辨性著作,作为师长,我感到欣慰,也深感时代的紧迫。
倪考梦在书中提出,自主不是抽象的“自由”,也不是虚无的“独立”,它是一个动态构成的系统。意愿、能力和资源三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真正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他特别强调了“资源”维度的重要性,并将其分为三类:个人资源、家庭资源和公共资源。其中,公共资源包括基建、生态等内容,常常被我们忽视,却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一个人的成长轨道与发展边界。他还特别指出,生态资源是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较难改变却影响深远的部分。
这使我想起自己在几十年前提出的“环境承载力”概念。在当年环境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时,我就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无限的索取,而是“共生的调适”;社会发展若想可持续,就必须以资源和环境为前提条件。那时候,我的很多观点被视为过于超前,但我始终相信,科学不仅是为了创造工具,更是为了厘清边界、确立责任。今天读《自主论》,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回应:年轻一代开始认识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只是他有多努力,也包括他站立的土地是否丰饶,他生活的城市是否友善,他所处的时代是否给予他足够的空间。
我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反复在各地强调这一点:人不只是生活在自然中,更是在自然的规训与馈赠中生长;人不仅要问“我想做什么”,也要问“我有空间去实现它吗?”这是资源的命题,更是公平的命题。
我是江苏淮阴人,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数学。我的老师周培源教授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他常说:“科学不是用来支配自然的,而是用来理解自然、敬畏自然。”我一生所学的数学与流体力学,也最终引我走向环境科学之路。那是1973年,我参加中国第一次环境评价调查,踏遍了北京西郊数百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次调查让我深刻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技术进步不能掩盖生态代价。
此后五十年,我致力于推动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并在1982年创办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建立“环境规划与管理”专业,并创建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后来我开始思考更加宏观的问题:如何建立一种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文明形态?也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并不只是对环境的保护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价值观的更新,一种发展观的转型。我提出“从三种生产系统看人类社会结构”:人口生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我主张“从尊重自然出发,建立起三生共赢的社会共识”:生态、生产、生活和谐统一。在这套体系中,人并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回应者——如果说自然是一种恩典,那么“自主”就是人类的回应形式。
现在,我看到倪考梦以他一贯的社会观察与政策实践,尝试在AI、大数据等技术话语中,重新建构“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公共资源的初始分配虽然大多由时代、地域等先天因素决定,但个体依然可以通过“用脚投票”(迁徙)与“动手实践”(改变)来争取自主。我很赞成这种行动主义的自主观,它将“命运的改善”从纯粹的个人层面,扩展到与生态、环境、制度、文化的互动之中。
而这,也正是我对未来生态文明的基本期待。生态文明的核心,不是让人回归山林,而是让城市、产业与自然达成一种新的和解。在倪考梦所倡导的“自主城市”理论中,我看到了一种可行路径:让年轻人不仅成为生活的参与者,更成为空间的创造者、规则的改写者。他们不必完全依赖既有结构给予的机会,而是可以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公共治理与政策制定,逐步扩展自己的资源边界,重建“人—环境”的新型协同关系。
我今年已经86岁了,但因为有信仰,我从不悲观。人类的创造力,始终来自与自然的对话、与他人的合作、与命运的交涉。《自主论》告诉我们:技术变了,规则变了,但人终究要靠意愿去发起行动,靠责任去承担变化,靠理想去抵御绝望。
我衷心希望《自主论》的传播,能为更多年轻人带去思考,也愿年轻人们都能在自然的怀抱中,坚定而温柔地走上属于自己的自主之路。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