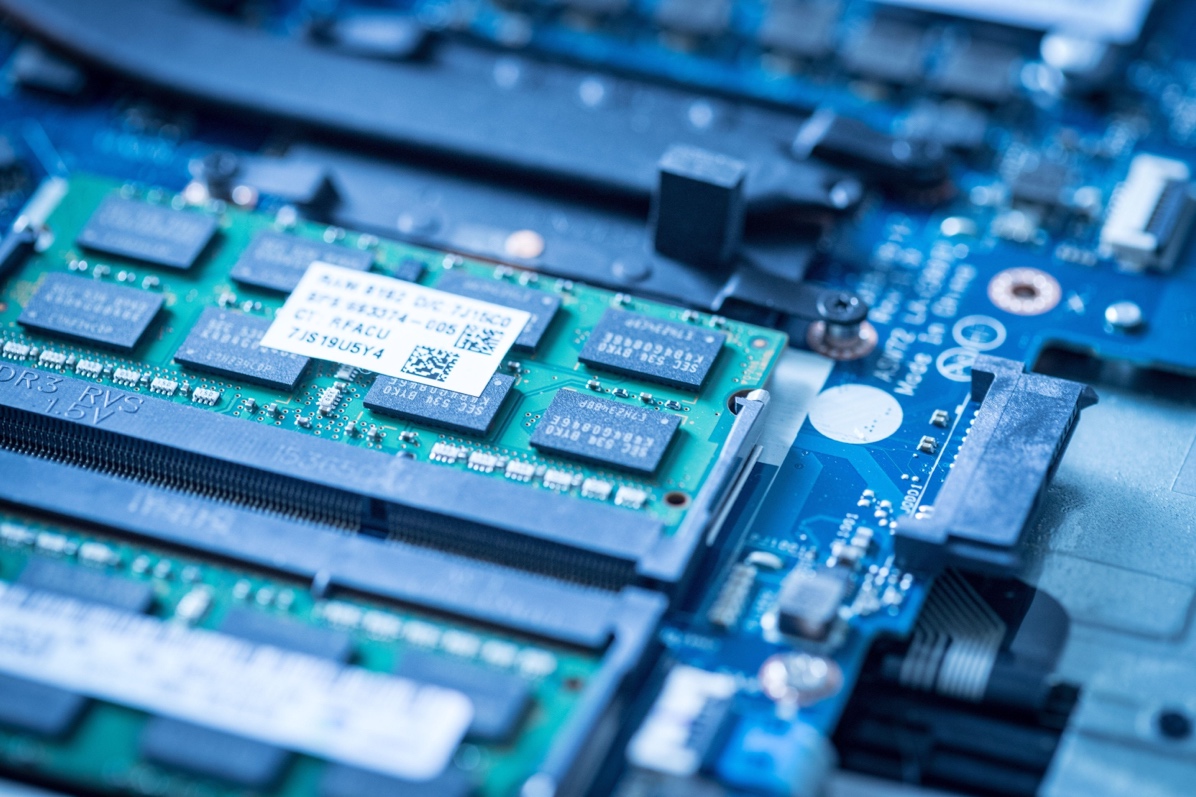从生存困境到诗性抵抗——赵应诗歌《当我们这些穷人谈起命运》的多维解构
赵应的短诗《当我们这些穷人谈起命运》(原载《黄河》2014年第4期),以冷冽的意象与悖论性修辞,构建了一个关于底层生存与命运博弈的隐喻空间,这首诗不仅是对物质贫困的写实刻画,更是对精神困境的哲学叩问。全诗如下:
当我们这些穷人谈起命运
风终将吹来,把我们这些穷人
抛向祖国日出时的炫目山河
命运就藏在喉咙中,难以启齿
有风是件好事,所有的九月之水
都会溅洒在街道上,启示我们
在一团陌生中黎明下行
当我们这些穷人心怀畏惧
连续几个晚上守着一盏油灯
谈起云霞明灭,大水决堤
妄想命运是一具早死的英魂
让墨水流尽,让打字机坏掉
让一切脆弱毛孔紧紧合上
此后便有泥土从掌中逃走
半截树枝画一个圆,有如骄傲
风终将吹来,掐灭一支烟头
一块大质量的烟云遮蔽了天光
当我们这些穷人谈起命运
命运也在日夜注视着我们
一、命运的凝视与反凝视:暴力美学的双向结构
诗中“风”的意象贯穿始终,既是席卷穷人的飓风(“抛向祖国日出时的炫目山河”),也是微观层面的暴力符号(“掐灭一支烟头”)。这种压迫性力量与“喉咙中难以启齿”的沉默形成互文,暗示命运既是外在的社会规训(如资源掠夺、制度性歧视),也是内化的精神枷锁。
尤其当“命运日夜注视着我们”时,凝视关系被倒置为双向暴力——穷人在被结构性压迫的同时,也成为以诗歌对抗命运的主体。这种辩证呼应了中国古代“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的张力:诗人以文字凿穿命运铁幕,使凝视本身成为觉醒的催化剂。
二、物质符号的消解与原始书写
诗中刻意瓦解现代性符号系统:“打字机坏掉”“墨水流尽”指向工具理性的失效,而“半截树枝画圆”则返归原始书写形态。这种解构暗合全球贫困线研究中“食物选择悖论”——穷人更倾向购买味觉满足的廉价食品而非营养品,表面是消费选择,实则是生存本能对文明秩序的无声反抗。通过“泥土从掌中逃走”的悖论,赵应进一步隐喻了土地伦理的崩解(如中国农村土地流失现象),而树枝画圆的几何暴动,则是对线性进步史观的解构。
三、时间政治的微观抵抗
“九月之水”作为农耕与工业时间的临界点,“黎明下行”的陌生化体验,解构了现代性时间秩序对底层的规训。油灯下的守夜场景(“连续几个晚上守着一盏油灯”)形成德勒兹式的“褶皱空间”,穷人在此展开精神游牧——谈论“云霞明灭,大水决堤”既是现实焦虑的投射,也是用自然时序对抗机械时间的策略。
这种抵抗与《贫穷的本质》中描述的“即时满足陷阱”形成对照:穷人因生存压力被迫关注当下,而诗歌却以延时性语言重构时间感知,使“烟头明灭”的瞬间,升华为存在主义的爆破点。
四、群体心理的黑色寓言
诗中“穷人”的复数主体性值得玩味:“我们这些穷人”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暗含内部裂痕。结尾“命运也在日夜注视着我们”中的“我们”,既是被凝视的客体,也可能成为互相审视的主体。这折射出贫困群体内部的复杂心理:如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底层往往存在“鄙视链”,而“妄想命运是一具早死的英魂”的集体幻想,既是对结构性暴力的控诉,也是对“诗人薄命”传统的戏谑颠覆——在赵应的诗学中,穷人的“失败”恰是抵抗庸常的英雄叙事。
五、在语言的废墟上重构尊严
赵应的诗歌《当我们这些穷人谈起命运》,最终在生存绝境中完成诗性救赎:当“打字机坏掉”宣告现代性叙事的破产,“半截树枝画圆”的原始姿态反而成为抵抗异化的最后堡垒。赵应的创作既延续了山西诗歌“以血为墨”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注入了90后诗人对后现代荒诞的敏锐捕捉,以黄土地的粗粝诗风,在命运的铁幕上凿出光隙,让穷人的叹息化作穿透时代的星火。
责任编辑:kj005
文章投诉热线:157 3889 8464 投诉邮箱:7983347 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