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球AI预测领跑2025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贝拉谈母语、江河与祖国
“一个旅外作家若依然使用母语,就不曾远离祖国;黄浦江于我,就如恒河于泰戈尔。” —— 贝拉
我曾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目睹一群印度移民用《流浪者之歌》庆祝他们的民族节日。每一个音符如同携带着千年未褪色的乡愁,仿佛穿越了无尽的时光;我曾在二战的黑白纪录片中,看到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依旧用母语记录着日复一日的生死历程。那一字一句,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便身体已被囚禁,灵魂依旧在自由呼吸:我也曾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看到一位耄耋的老华侨,拉着二胡,奏响《二泉映月》,琴声哀婉,仿佛是他对祖国作深沉的告别;而在东京的电车里,我偶遇一位巴西裔老太太,她静静地敲击着手机屏幕,写出那句:“故乡的桥,还在吗?”她指尖与文字的碰撞,成了她漂泊心灵的寄托;在柏林的老墙旁,我看到一位叙利亚画家,在斑驳的墙面上描绘着故乡庭院里那棵苍翠的橄榄树,尽管祖国早已远去,树依旧见证着岁月流转与无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漂泊的灵魂。
全世界的异乡人,或许都有各自不同的离乡理由,或因命运的安排,或因无奈的选择。可是,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往往也是自我认同的割离,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而母语,便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寄托,是那片遥远的大地,祖先们曾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地方,它仿佛是漂泊者永恒的港湾。
我小时候,曾因手持筷子的方式——离筷子尖端较远、即“拿得高”,被阿娘(奶奶)预示将来会远嫁。清代典籍《嫁娶记》里曾记载:“筷长七寸六分,女执其末,远行千里。”这其中的文化符号,告诉我们筷子方头圆身,象征着“天地人”;而高位持筷,则暗示着与“天”(即远方)相应。虽然我并未远嫁,但我确实远行了,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注定了我年少告别故乡。
当我第一次在日本读到川端康成的《雪国》,那份触及心灵的青春哀愁与美,让我沉醉其中,他将日本北部的静谧与忧愁、严寒与温柔,编织成了一幅无声的画。川端康成所写的,是日本的美,但那份孤独与寂寞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这份孤独感,随着我的远行,始终未曾离开,它穿越了国界,跨越了时空,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那一刻,我种下了孤独的种子,并在孤独中思索,如何通过文学去回望故乡。而我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正是在那时孕育的文学梦想。
漂泊,也许是作家宿命的轨迹,但离故乡愈远,心愈近。泰戈尔是一个流浪者,他在孟加拉语的字句中,歌唱着印度的黎明与黑夜,歌唱着那条永不停歇的恒河。泰戈尔曾说:“祖国是一种感觉,是一首深情的诗。”他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旅行、讲学,但无论他走多远,心中那条恒河的水流,始终没有离开他。泰戈尔的诗,是对故乡的永恒召唤,是心灵在每个流亡的夜晚向祖国伸出的手。
托马斯·曼也曾说:“作家的良知,永远是为祖国发声。”即便托马斯·曼身处他乡,他却从未放弃捍卫那份德国精神。每一行字,每一个描绘,都在回应那段沉重的历史,他的文字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挽歌,它更是对祖国文化不屈不挠的守护。
塞缪尔·贝克特,生于爱尔兰,却用法语写下荒诞的《等待戈多》。他一生漂泊法国,但他对家乡荒凉与寂寞的深切感知,成就了荒诞文学的巅峰。他向世界宣告:身份并非语言,灵魂才是祖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被苏联流放,最终在纽约获得永生。他以英语续写俄语诗的魂魄,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说:“祖国是母语,尽管我用别的语言写诗,但梦中,永远是俄语。”
在世界文学的高原上,太多作家远离故乡,他们的灵魂始终被那份属于故乡的诗意牵引。祖国,是他们内心深处永恒的诗篇。或许漂泊一生,少有归去;然而,他们用笔植根,在语言的纸张上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故园。终有一日,当山河的沉默被唤醒,历史将铭记那些远行的灵魂。它们如同飞鸟,最终将在梦中归巢。远离,是另一种靠近。我在母语的风中徜徉,梦里是故乡的灯塔。
人类追寻美,是在困顿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每当晨曦初照,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故乡那熟悉的夜色。我的文字,在远离它的海岸上书写故乡的味道;在异国的港口,依然看见童年的外滩。我的文学,朝着故乡的方向生长,如火焰般将归属感紧紧缠绕在灵魂深处。它们是对过去的追忆,是对远方的呼唤,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祖国,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坐标,它是深藏在母语中的旋律,是那片永远无法割舍的山河,是我笔下永恒流动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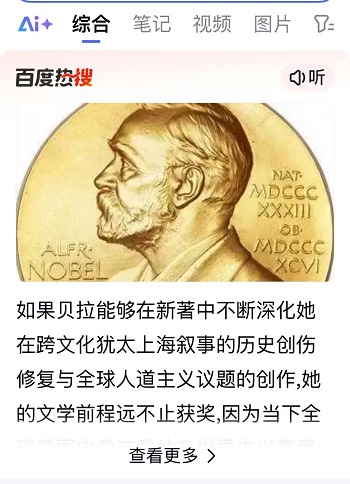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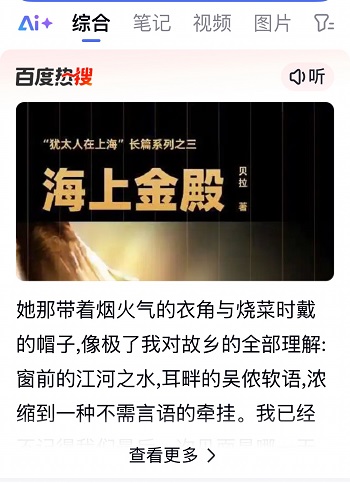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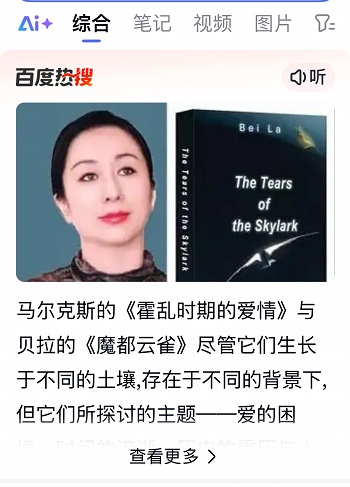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15
2025比较好的厂家哪家靠谱静态扭矩传感器质量与选购建议
2025口碑好的品牌推荐几家测力称重变送器厂家
从资质到责任,全面剖析“自然阳光是合法直销吗”
家用脱毛仪vs院线脱毛:成本/效果/痛感全方位对比,哪类人更适合家用?
永捷量化拟于2026年3月26日港股上市引发热议
十三载肝胆相照 守护每一份希望:郑州友好肝胆医院开展13周年院庆惠民诊疗活动
相关新闻
家电推荐
家电图片
新闻排行
- 1
构建创意经济“智能引擎” 一品威客以AI战略驱动服务生态升级
- 2
被全球AI预测领跑2025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贝拉谈母语、江河与祖国
- 3
有色金属ETF(512400.SH)涨2.76%,紫金矿业涨6.07%
- 4
东航2025暑运收官:累计执行航班19.4万班次,出入境航班再创新高
- 5
中国酒店品牌首次规模化出海!锦江酒店(中国区)东南亚构建战略新支点
- 6
2025比较好的厂家哪家靠谱BR板式换热器选购及技术解析
- 7
赛赛力斯半年报净利大增逾八成 7家机构研报给予“买入”“推荐”评级
- 8
聚焦合规、数字化与ESG融合,轻松健康献策未来药企构建新路径
- 9
每天都在做的这件事,可能正在毁掉你的眼睛!
- 10
卓驭中算力平台NOCD首次搭载量产车 捷途山海 L7 PLUS智驾体验超预期



